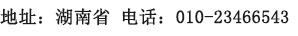白癜风知名专家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171222/5951583.html文/刘向忠一我的村庄坐落在一座大山山头的平地上。站在村庄里看,三面远远的环山。因地势高低和山脉走向,散落分布着几十户人家。据老人说,这里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人了。我们的院落位于村子中央,和许许多多院落一起成为这个村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条不宽的夹道(巷道)从东到西约米。村中一南一北两条曲折的山路通向外界。村头东面又分为三条大路,大路中又分出不同的小路,血脉一样连续、延伸到广阔的原野、沟道、大山和森林;西面也延伸到一个山头上。村庄中,曾经有几个显眼的所在,一个是占地近十亩的麦场,一个是牛场,另一个是驴场。还有一棵树冠茂密、树干阔大的核桃树。时光流逝,岁月变迁。这些与人畜兴旺,烟火鼎盛的村庄一样已不复存在。过去麦摞稠密,麦草堆积如山的大麦场成了几家人的院子;曾经牛羊成群的牛场成了队长家的财产,圈院盖房,显赫一时;驴骡欢叫的驴场归支书家所有,他们大兴土木,好不气派。村庄标志一样生长多年的巨大的核桃树也早被树主砍伐殆尽,枝叶不存。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不知道他们通过怎样的手段不声不响的把集体财产据为己有。现在,这些场所大多都已闲置,弃之不用。这是我的村庄沉重的一页。这次写下我的村庄,我是愧疚的,难以释怀的。曾经炊烟袅袅、人欢马叫、沃野厚土的村庄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回味和念想:树木花草果实的清香怡人,山坡河道森林的多彩神秘,黑土地*土地红土地的丰盈饱满,庄稼泉水的茂盛生机,小麦洋芋胡麻豌豆玉米的光泽馨香;成长的足迹,生活的轨迹,生命的图景;家禽家畜的顺从听话,家具农具的朴实亲近,父母的叮咛嘱咐牵挂历历在目,村人的呼唤喊叫犹在耳边回响……自从父母亲离开村庄在县城生活以来,我有好几年没有回到我的村庄,没有看到我的老家。母亲说,我们的村庄还有近10来户人家依然留守。他们在沧桑、萧条、清寂的村庄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枝头的喜鹊也没有以前叫的欢实,数量众多的麻雀日渐较少,杏树、梨树的花朵和果实也不再灿烂和繁密,路边、沟道、田野里蒿草、冰草疯长,各种树木、花草兀自摇曳着、孤独着、守望着。荒草、荒芜的气息弥漫在时空中,被孤独的风吹动着,被寂寞的太阳照耀着,被孤单的月光沐浴着。二年年底,哥哥从亲戚那里得到确切消息:因我家院落老房子闲置无人居住,有人看上了我家院落的位置,要私自搞养殖或种植。我们心里知道,这里是父亲母亲的劳作之地、生活之地、生存之地、生命之地;这里是我们兄弟四人的出生之地、成长之地、生活之地、生命之地;这里也是父亲的终老之地,是他最后的愿望。在哥哥多次奔走、央告和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我家历经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院落和瓦房被拆除推倒,夷为平地。父母没有了家,我们兄弟没有了老家。我们真正成了回不去故乡的人,成了回不去老家的人。千变万化,恍然如梦。我才觉得没有老家的人就像浮萍,失去了真正的根基,失去了生命之源。无论走到哪里都漂浮不定,心神不宁,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守舍,空空如也。哪里有老家温暖、踏实、可靠?哪里有老家清净、安宁、包容?对于我的村庄,我是负疚的。对于我的老家,我的一生将是负疚的。就在老家的院落和瓦房被推掉抹平消逝的前夕,我竟然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没有回去看上一眼,没有留下一帧照片,没有跪拜,没有挥泪,没有告别;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哭泣、长叹、惋惜……这就是打工人如我者的无奈、宿命、悲哀和不甘。我从父母亲恋恋不舍、黯然伤神地带回县城的物品中,轻轻拿了两样东西,一顶草帽,一口小铁锅。只有这两样东西和父母兄弟成为我对遥远的老家的亲近、思念和感恩。在我的小家,这顶略显褪色、发*的草帽也算安了新家,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应有的位置,也会长久地保存下去。对我来说,他就是故乡,就是老家。因为他带着父母兄弟的气息,带着风雨阳光的气息,带着庄稼晨露的气息,带着花草树木的气息,带着泥土果实的气息;带着太阳的味道,带着月亮的清辉,带着星星的微光,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三草帽,作为农业农耕生活文化中重要的一员,在乡村广阔的天地间发挥了无所不有的作用。在田野,在山道,在庄稼地里,在大麦场,草帽成为亲切而又温暖的风景。它与风雨、骄阳、土地、农活、农人、果实息息相关,沐风栉雨,相随相伴,经年累月。过去的岁月,村庄里的人们是没有雨伞雨衣雨鞋的,草帽成为人们遮雨避雨、遮阳防晒的重要用具。家家都有大小不一,形状相似的几顶草帽。每逢麦*时节,村里的几位婆婆都要亲自去麦地选来选去,折上些匀称、饱满的麦子,带回来掐掉麦穗,再把麦秆浸在水中,反复好几次,等麦秆柔软、劲道时,用自己的巧手为家中编制几顶适用的可爱的新草帽。我家里常年使用的几顶草帽都是父亲去赶集时捎带着买回来的。只要人们外出劳动、赶集或到大山里放牲口,总要从屋子里拿出一顶草帽,戴在头上。天气转阴落雨时,随时随地可以防止淋湿头发和肩膀。下大雨的时候,人们只好小跑到茂盛的大树底下,或躲到崖坎底下避雨,等雨变小的时候,才落鸡汤似的一脚水一角泥,一步一滑地走回家。然后小心翼翼的把草帽挂在屋外,晾干后,再拿回屋里。我上中学时的那几年秋天,雨水真是多,一下一月左右也不见天晴。人们出不了门,吃的水,洗衣服的水,牲畜喝的水便都是无根水——雨水。麦地里的麦码子上,麦场里的麦草上,麦摞上的麦粒都发了芽,长出了半截绿色。大人们戴上草帽,手握一把铁锨,一次又一次地去麦场里瞧瞧,去田地里看看,还不时抬头凝望阴云密布、雨水连连的天空。是啊,老天爷要下雨,人们再着急再担心也无济于事。中学在大山下面的乡上,路途较远,平时大约需要走40分钟才能到达。这时候,我们的上学路就更加难走了。我们戴着草帽,穿着夹夹(旧衣服缝补成的没有袖子的厚些的衣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弯曲、陡滑的土路上,尽管都小心谨慎,但稍不留神就会滑出几步远,也会摔倒,我们裤子、上衣都会粘上不少泥水。我们一把雨水一把汗水一把泪水的一步步向前移动着,有时候大笑,有时候叹气,有时候埋怨,有时候互相拉一把……好不容易走下大山,经过长长的巷道,来到学校,我们浑身几乎都湿透了。进教室之前,我们便把草帽摘下来,把夹夹脱下来,放到教室外的窗台上晾着……四村庄每年的苦夏时节,太阳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田野里的色调也明亮了许多,丰富了许多,迷人了许多,醉人了许多。一波又一波热浪把冬小麦成熟的气息和味道吹得天地间到处都飘溢,村庄似乎微醺了,人心也似乎微醺了。人们再也不能四平八稳、无所顾忌地干其他事情了。人常说麦*一晌。龙口夺粮。早上或下午,大人都要去麦地里看看麦子的成色,并随手掐上一个饱满的麦穗,放在手心,双手揉碎,轻轻吹掉麦衣,再把麦粒小心地丢进嘴里,咀嚼、品咂麦粒的饱熟度和硬度,估摸能不能下镰收割。这时节,人心是喜悦的、澎湃的,充满期望的,也是不安的。这时候,大大小小的草帽可就派上了大用场。大人、小孩都戴上一顶,拿上早已磨好的镰刀,带上开水、干粮;大人还要背上一个小背篼,或提上一个拢子,急切、欢快地来到自家的麦地,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在地头阴凉处,开始挥镰收割。远远近近田野上的麦地里,随处可见一顶顶草帽,朴素的花朵一样绽放,闪动,大海上的帆船一样动荡,移动。火热的阳光泼洒,热风吹拂。一块块发光发亮、熟透熟美的麦田,像田野里新生的一幅幅丰盈饱满、色彩诱人的画卷,令人欢欣鼓舞,心醉神迷。目睹着家里已经完全成熟的麦地,我心里是激动的,兴奋的,美好的,这是劳动苦累之前真镇真切切的感受。往往是一早上或一下午,父母亲和我们兄弟并排半弓着腰开始割麦子,左手握住麦身,右手挥舞着镰刀,先割上一小把,拧成“腰”(捆小麦捆用),然后动作娴熟地割掉一捧又一捧,接着捆成一个又一个大小一致的麦捆。齐刷刷地排成一排排。热流、麦叶、麦芒、麦秆、杂草、泥土混合的气息侵袭着我们的手和脸,觉得痒酥酥,还有轻微的刺痛感。我们不时摘掉草帽,擦擦脸上的汗水。我看到父亲的衬衣后背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割上一段时间,父亲让我们停下手中的活,坐下来喝水、吃馍、休息。这时,草帽就用做了扇凉风的工具,真是太受用了。手握帽檐,轻轻的一下一下扇着风,奢侈的风一跳一跳地吹着我们发热、红彤彤的脸庞,觉得好舒服,再回头看看割过的麦地,几排排麦捆整齐地躺在地上,麦茬齐刷刷地横在眼前,那舒服、满意的感觉贯通了全身,身上的疲累也似乎减少了不少……到中午或傍晚收工的时候,母亲先回去做饭,我和弟弟拉麦捆,父亲和哥哥要把麦捆并排码成一个个数量相等的麦码子,再用两个大些的麦捆戴上“帽”,避免雨淋。等所有地里的麦子割倒之后,经风吹日晒雨淋,麦码子也干了不少,轻了不少。然后人背驴驮架子车拉到麦场里,一层又一层摞成一个又一个山头一样的麦摞。有时候,大人会在劳动的间隙,揪一些豆角、大豆,摘一些杏子、梨、野果,拾一些麦穗、洋芋之类的果实,放在草帽的帽碗,捧在手里端回家,这些都是小孩喜欢享用的食物。五碾场的时候,更是离不开草帽。碾一场麦子,需要十多个人忙碌。选上好的天气,摘掉草摞上的帽,撕开麦摞,解开一个个麦捆,均匀地摊上一场麦子,用骡马驴牛或拖拉机开始碾场。碾上一段时间,要抖场,大人小孩戴上草帽,拿上木杈一起上,从中间或边缘开始,一圈又一圈地抖动抖乱麦秆,让麦粒沉到底层。这时,麦穗、麦衣、麦屑、尘土一起飞扬,呛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有时会被后面的木杈挑起的杂乱的麦秆掀掉头上的草帽,我们赶紧往前走着,拾起草帽,戴在头上,继续抖场。第一次抖完之后,再开始碾,这样要持续三遍,直到所有的麦穗脱落成为麦屑,所有的麦秆变柔软成为麦草,一层金*可爱的麦粒铺到最底层,才开始起场,将所有的麦草不停地抖动着,让里面的麦粒几乎落尽时,再把柔软的麦草聚拢,然后一木杈一木杈地端到一边,摞到一起。等麦草挑尽了之后,再把麦衣混合着的麦粒推到场中间,开始扬场。父亲、哥哥用木掀一下一下扬到半空中,麦衣被风吹到一边,麦粒在另一边落下聚拢,母亲则拿着扫帚掠场,就是不停地用扫帚掠掉落在麦粒上未碾碎的麦穗麦秆等杂物。父亲、哥哥戴的草帽不时被风吹掉,随风跑到一边。母亲戴的草帽上唰唰唰地落着麦粒。当一大堆麦粒小山头似的堆起来时,扬场的活就结束了。一大堆崭新的麦粒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的、迷人的光泽,让人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快意。蹲下来,抓起一把麦粒轻轻抚摩,麦粒快速地从手缝滑落,那感觉就像能把人心融化了一样,一天所有的劳累都飞到九霄云外了。每次往塑料袋子里装麦子时,哥哥总要用木掀在麦堆周围画一个圈,还要给麦堆戴上草帽……六有一个暑假的一天,我们去远处放牲口。傍晚时分,我们赶着牲口从一个高高的山头往下走。此时,一天的暑气消退了。清风拂面。我惊喜地看到田野里一片片绿小麦在山风吹拂下,波浪似的不停地涌动着,涌过来涌过去,涌过来涌过去,让人晕眩,欣喜若狂。我们都被眼前的风景画吸引了,愉快地大呼小叫着,奔跑着。我兴奋的竟然把戴在头上的草帽摘下来,随手甩了出去。在风的作用下,草帽鹰一样高高地飞起来,快速地钻入山坡下波浪翻滚的麦田,瞬间不见了踪影。我一下子傻了眼。当时太激动了,我并没有看清帽子究竟钻入到了哪块麦田的哪个位置。山坡下的麦田太多了,而且看上去都是一个样,我走过去走过来,跑上跑下,任凭我怎么寻找都没有找见我甩出去的草帽……七多年前,我在《十月》杂志读到福建作家黎晗的散文《夜里戴草帽的人们》等,颇有感触地写下过一段话:这样的文章不仅能让人耳目一新,怦然心动,也能警醒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