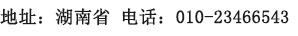“艺”起筑梦生态大理之肆拾陆
走进生态文明
新时代
树皆菩提
我常常喜欢坐在树下。
坐久了,站起来伸伸腿,弯弯腰,作几次深呼吸,头脑便清晰异常,心情亦释然惬意。
坐在树下是因为树的诱惑。喜欢坐在树下的人不止我一个。树在生长过程中根本没有与人有关的动因。因为四季,只与日月有关;因为生命,只与物质有关。
人喜欢坐在树下,是人的福气;树站在人的背后,是树的施舍。
我喜欢坐在树下还因为我种了许多树,这许多树便自然地归属于我。许多喜欢树也喜欢坐在树下的人却没有树,他们中有的人想种树却没有地方,有的人有地方却不懂得种树。
我喜欢坐在树下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并非刻意要去实现什么。在坐着的时候,眼睛极自然地看到前方的景物。接着,又从前方的景物中延伸出一些想法来。这些想法,有的很清晰,有的很朦胧。想着想着,便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现象出现。
眼前的坝子里,仟陌纵横,鸡鸣狗吠之声相闻。翠绿的田野包围着的村落,自然是因地而建因景而生。为此,田园在眼前舒展,牧歌在耳边传唱。
公元前五百六十五年的一个平凡的日子,紧邻印度的尼泊尔的一个普通的农夫家庭里,诞生了一个此后惊天地、泣*神的不同凡响的孩子,名叫释迦牟尼。
他一睁开眼睛,与其他的孩子一样,看到了同样的太阳同样的月亮,以及田野村舍、花鸟虫鱼。不同的是,他还看到了他亲爱着的人和亲爱着他的人,正在蒙受着的及还未来到的 苦难。由此,一个如何解救 苦难的心结,便早早地编织在他幼小的心里。
走很多路,历很多事,这是开启智慧完善智慧的 途径。不同的是,释迦牟尼长成之后,揣着无限困惑,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印度菩提迦耶的一棵菩提树下,一坐就是数年。
这数年的时光,在他紧闭的双眼前飞快地掠过;日月星辰,雷鸣电闪,四季寒暑,孕育出他脑海中的源于人世间又超越于人世间的思想精髓。佛教的解救众生,超渡众生的高智慧的哲学要义就此诞生。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神清气爽的释迦牟尼睁开了双眼。一棵普通的菩提树,成就了一位让世人顶礼膜拜的佛祖。
在我知道这个故事之前,就常常喜欢到树下坐着。老家古城西郊有一棵巨大无比的老缅树,树上难见天光的枝叶间,有喜鹊筑成的圆圆的巢;树下一地落果的日子里,有一群群啄食籽粒的红褐色羽毛的鸟。这便是一方顽童们的 ,里面有我。而我,有时也会一个人到树下去,心是茫然的,呆坐很长时间。偶尔,也会或坐或卧地在树下睡着了。睡着了的时候,能感觉到从脸上吹过的风,落到身上的摇动的阳光;能感觉到头顶喜鹊振动的翅膀,进入耳朵的身边鸟雀的啁啾。做梦也是常有的事情,有时,我会梦见自己成了一只喜鹊,把喜讯告诉给临福的人家;我会梦见自己成了一缕阳光,把光明和温暖贴在某家阴冷的窗上。
在山地生活的日子里,我是不能不到地里去指导做活的。这个时候,我会极自然地找棵树坐下,背倚着树干。眼睛呢,可以看着雇工们劳动的场景,也可以看看天空和四围。当然,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如何把成本再降低一些。这些想法是必须的和迫不得已的。尽管,这些想法会让人很累。
轻松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太累了的时候,看着眼前的坝子,坝子里密集的村庄,便会想到:我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我有许多果树,他们没有。我能很随意地在某棵树前坐下,他们没有某棵树可以随意坐下。接着,一些很哲理的念头就会冒了出来。
这就是:他们能想到的我一定能想到,我能想到的他们不一定想到。犹如飞来飞去的鸟群,让我很容易地想到它们和森林的关系;还有野兔和田鼠,它们和土洞的关系。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即便一粒微尘,也离不开它所以能存在的诸多关系。
那么,人呢?
人是一个复杂善变的群体。他们缺乏植物的顺应性和恒定性,缺乏其他动物的客观性和适应性。因此,他们在非常聪明着的时候又非常愚蠢。聪明在于他们能够自己制造灾难而无法消除灾难,愚蠢在于他们用聪明干着错事的时候还沾沾自喜。
因此,释迦牟尼从一个普通的人升华为一个不平凡的佛。成佛后的释迦牟尼又把自己下降到人。他说:“佛无处不在”。又说:“佛在你心中”。释迦牟尼把人分为灵与肉两个部分,他竭力拯救的是人的灵的部分,即精神。精神主宰着人类的世俗世界的时候,有着真善美更有着假丑恶。精神主宰着佛的世界的时候,佛的世界里只有真善美而了无假丑恶。
释迦牟尼发现了人类发展必须要调解人类精神世界的哲学方法。因此,他成了无数历经苦难的信徒们顶礼膜拜的佛祖。
我在树下坐着的时候碰到一些有趣的现象。这些现象让我很容易地拯救了一棵树甚至许多棵树濒危的生命。首先,在果园的中部有三十余株花红树。这些树的果实都熟在其他品种之前,一个挤一个的红红的果实把树枝压得垂了下来,惹得让这时上山的客人欢呼不已。这是一些不计成本、不计收入的树种,一定是被雇工中的管理者疏忽了。常常,他们在死了一棵树的时候是不告诉我的,只有死了若干的时候才让我知道,让我无比心痛。
我在一棵花红树下坐着的时候,因为那里的草很干净很柔和。同时,我让挂满果实的树枝挡住所有的阳光。地上还有一些掉落的花红果,我挑了一个个大红艳的慢慢咀嚼着。这是一个惬意的时刻。不过,腰部痒痒的,有东西爬在了我的皮肤上,一摸,一个巨大的张牙舞爪的蚂蚁被捉在手里。
树根周围有许多蚂蚁,它们从一个洞里爬了出来,向那些落果爬去。这时,它们的食物是充足的。不过,有一根露出地面的树根,光秃秃地没有了皮层。这让我想到那些死去的树根,同样地没有了皮层。真相很快大白了,这些可恶的蚂蚁们,是它们在人的眼睛不容易看到的根部距土层很近的地方,把树皮啃食了一圈。然后,又把嘴巴伸到土层里面。
人需要的是果实。为了果实,人会努力地去管理果树。蚂蚁需要的不仅是果实,还需要树的根皮,以至让树死掉。那时,我已经想到了既解决问题,又让蚂蚁愉快的方法。不过,我还不认识释迦牟尼,因此,我采取了让树活着让蚂蚁死掉的方法。
我在另一棵树下坐了很久,为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这件事的因和果都集中在成熟了的梨果身上。过程很简单,邻村的偷梨人被抓住他的人打了几下。然后,所有的偷梨人要讨个公道。因为,承认偷梨是不对的,但梨不值钱;而人是无价的,人是不可以被打的。这件事让安静的果园热闹了很长时间,让主持调解的警察也费了不少口舌。当然,一切大事都得化小,一切小事都得化了。
我在树下坐着的时候,并没有想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不能对偷梨的人说你偷梨是对的,我也不能对打人的人说你打人是对的。大凡世间事,也都应该有个是非标准。不过,当人在清醒的时候,标准是明确的,当人被欲念蒙蔽了的时候,标准是模糊的。
一时之间,我的心情糟糕到极点,一种失望的情绪,弥漫了属于我的整个空间。我累了,累得直想闭上眼睛。这时,一只长尾巴的拖白翎从眼前飞过,似乎还对我叫了两声。我顺着它飞行的轨道,看到远方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看到绿树迎着阳光展现的剪影。此时,我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事情。
我走下山去的时候,我对偷梨的村民说:“你们中确实有人被打了,让被打的人来打还我吧!”
被打的人没有来打我,被打的人也没有再偷梨。
以预测学为生的大师马馨泽先生开了辆奔驰车到大理来,找到我的时候,他说:“要做两块匾,送到佛教圣地鸡足山的三圣殿去。那里的住持要八个字,每匾四个。这字,就请你题吧”。
马先生曾经是云南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在滇南某地谋到一个不错的饭碗。一念之间,他辞职在省城昆明的圆通街上,挂出了预测天地*神、风水吉凶的牌匾,一挂就是十多年。易学与佛学本是两个概念,但大凡宗教与高智慧的学说之间,总有一些姻缘关系,互为渗透。因此,马先生不远千里,辛劳奔波,必定想用已掌握的中华民族的峰巅学问,与远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释迦牟尼握手。
“树皆菩提,心可涅槃”。这八个字是我脑中灵光一现,瞬间跳了出来的,得到了马先生的首肯。
果园与邻村之间,有一座佛教寺院,叫慧明禅寺。每年的香火会期,总是热闹非凡。大约进庙之人,总免不了有所敬贡,顶礼膜拜。这其间,香客们指望的是庙内神明保佑自己,保佑全家。殊不知,在极其平凡的日子里,都可以找棵大树,倚树坐下。在闭目养神之间,淡漠 俗事之时,自会有些明晰的意念跑了出来,让自己心静神静,找到自救或救人的方法。
树皆菩提。我种了许多树,坐一棵就行了。还有许多树,等待着那些无树可坐的人。但是,他们会来吗?
文稿来源:《山地的事》刘绍良著
(注:无署名配图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来电,我们及时删除)
责任编辑:左家琦
----END----
请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