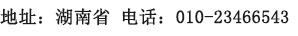春山如笑(下)
竟然没躲?
女侠愣了愣神,少年郎笑着环住她,她就整个儿倒在了他的怀抱里。
梅香幽幽,雪花柔柔,冬风也许极寒,但已经没人察觉了。
相玉儿错愕地瞪圆了眼睛。
那黑黑的眼珠里映着一个人,乌发金冠,眉目里淌着难以遏制的温柔。
柏翊沉默着伸手合上她的眼睛,在她纤长的眼睫上,轻轻落下一个吻。
「你……」她想说话,可心跳声如擂鼓,一声接一声,让她的思绪全数化作了空白。
柏翊惯常带笑的脸上没了表情,像是难得的认真。
他的目光宛如浩瀚的星夜,近在咫尺,却有万里之遥。
叫人读不懂,猜不透。
相玉儿愣住了。
柏翊闭了闭眼,像要控制某些即将泛滥的情绪。
然后他睁开眼睛,伸手摘掉了她的白玉冠,系发的红绸带握在他掌心,像摘下了一面旗帜。
「我动一动美人计,你就输了。」他低头拉过她手腕,红绸慢条斯理地在她腕上打个结。
原来只是授课。
长发散了满肩,映着相玉儿一张素白的脸。
相玉儿垂下眼睫,撑着雪地站了起来,红绸带在风中飘舞。
她酸涩地盯着那整齐的红色系带,恍然一笑:「是啊,我输了。」
她输了。
他只是暧昧地靠近,她就忍不住把真心交出。
她早知道他容易让人沉沦,明明只是浅交,却能表现得那样深情。
但他用日复一日的呵护让她失了神放了心,让她一步步退无可退,自投罗网。
可她又这样绝望地发现,在靠近他的那一刻,她的心竟然跳动得这样厉害。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叫人难受呢。
驳礼那天,相玉儿独自一人前往王都。
宣平侯派人为她送行。
是那小贼。
小贼说:「侯爷没找到春山如笑,说要姑娘自己多加小心。」
相玉儿头也没回,说:「知道了。」
小贼又说:「侯爷说情字一途最难走,姑娘你生性聪慧,莫要在同一个地方跌两次跟头。」
这回她沉默半晌,才应一声:「知道了。」
小贼还待开口,相玉儿冷冰冰道:「你们侯爷怎么这么多废话?」
小贼委屈,「最后一句话了,其实是我想说的。」
相玉儿望天,「你说吧。」
小贼期期艾艾道:「能事成最好,可若不能事成,侯爷未必真会狠心让左徒大人死。」
相玉儿这才仔仔细细地打量小贼,将这唇红齿白的小贼看得脸红,她才没头没尾道:「从前夜黑没发觉,你这长相,倒与我一故友有些相似。」
小贼害羞捂脸道:「大约好看的人都有些相似,侯爷曾说我长得与左徒大人也有些相似呢。」
白天的灿烂阳光里,小贼临水自照,嘿嘿笑得像个小傻子。
相玉儿失语片刻,翻身上马,逃也似的离开了游水国。
驳礼有三日,第一日满街花灯如星,第二日满城弦乐齐鸣,第三日万民来贺万岁。
相玉儿便是在第一日的*昏到的都城。
天色渐暗,橙色霞光浓淡不均地缀在地平线,深蓝的天幕上一弯新月浅浅。
各色灯笼都已经摆上了,五颜六色的灯纸被火苗一照,透出斑斓绚丽的色泽来。
街上热热闹闹,随便看个什么人都是喜笑颜开的模样。
买卖东西的商贩与主顾带着笑,讲究的是和气生财。
拉着手不害臊的小情人带着笑,实在是心里的欢喜藏也藏不住。
在河岸边放河灯的妇人们带着笑,是希望上苍垂怜让渺小心愿都能成真。
相玉儿穿的红衣,却是一身寂寞的红衣,没有笑,笑也笑不出来。
她与周遭拉开了距离,审慎地做个看客,只用眼看,只用耳听,唯独不动心肠。
她一路走走停停,偶尔被人群拥挤着去猜灯笼上的字谜。
有梳羊角辫的小奶娃想要一盏宫灯,哭着拉奶奶的一角不肯放手。
奶奶的布衣上有许多补丁,小娃娃的衣裳却浆洗得干净。
相玉儿一时失神,走上前去付了钱,把宫灯拎给小娃娃。
小娃娃忘了哭,睫毛上还带着闪闪的泪珠,就咧开嘴握住了灯把。
穿补丁衣裳的奶奶头发花白,慈爱地看看孙儿,又慈爱地看看相玉儿。
「好孩子,你像是有什么心事。」
相玉儿木了一天的脸了,她伸手搓搓面颊,非得对老奶奶露出个笑脸不可。
「我没有心事呀,我能有什么心事呀。」她笑,眼睛眨呀眨,比羊角辫还单纯。
奶奶撇着嘴摇头:「你这笑呀,可真是比哭还难看。」
相玉儿于是不笑了,又木着脸,爱看不看。
奶奶拉她在河边坐下,千百盏河灯从水面上漂过,拥拥挤挤,争先恐后。
「你看这灯,多傻呀,前面哪有什么仙人在等着它们,可它们偏一厢情愿,自投罗网。」她折了梅,揪了花,一朵一朵地,都去砸那愚笨的河灯。
叫它们听信*话,叫它们自作多情,叫它们把心输了个彻底。
小娃娃拎着宫灯,瞅瞅她,再瞅瞅河灯,答非所问:「可是它们多好看呀。」
相玉儿跟小孩儿斗起嘴来:「好看就有用了吗,好看就不傻了吗?」
孩子答不出来,握着糖葫芦不再理她。
奶奶说:「不管仙人是真是假,可它们却因为仙人而有了此刻实实在在的美。这就有用,这就不傻。」
相玉儿不再说话了,她仰着头看那一弯月亮渐渐爬高,看那一弯月亮慢慢放大。
月光漫漫,在她眼眶晶亮的泪水中。
驳礼第二日,满城皆是丝竹声。
小船儿悠悠,载着飘忽的琴声顺水而下。
拱桥石狮子一百零九只,七个乐师倚着狮子吹吹弹弹。
岸上楼阁影影绰绰蒙了道雾纱,达官显贵们坐着喝酒听曲儿。
红楼底下挤了一堆人,急躁地仰头看上面。
锣鼓敲了三声,好戏才缓缓拉开。
原来是个戏台子,借了皮影戏的形,玩的却是戏法。
一道白幕把戏台挡了个严严实实,台上人影悉数投在白幕之上。
先瞧见一棵大树,大树底下一块大石,大石上躺了个人,是男是女分不清。
石头上缓缓升起两翼,原来是只蝴蝶,蝴蝶翩跹,从台东转到了台西,再从台西转回了台东。
再回头去看大石上卧着的人,却已经消失了。
原来这一出演的是梦蝶。
蝴蝶犹自飞舞了一会儿,看客们渐渐不再稀罕,抱怨着让舞姬开始下一幕。
而白幕突然落下,戏台里竟然空无一物,大树、大石都消失不见,竟连产生影子的烛光都一起消失了。
看客们又睁大了眼睛鼓掌叫好,相玉儿跟着拍两下手掌,一双眼睛四处找啊找。
总该有机关,总该有障眼法。
世上可没有那么多神迹,有也不该出现在这里博小民一笑。
她转着脑袋处心积虑想解谜,戏台之上红楼之中竟然凭空多了只蓝莹莹的蝴蝶。
蝴蝶振着翅膀款款飞来,乖巧地栖息在她的肩膀。
戏台下又是一波热烈的鼓掌叫好。
贺她好运被蝴蝶相中,要她为红楼戏法抚乐收尾。
看客们簇拥着傻眼的红衣少女往前走,红楼主人非要送她一把琴。
琴是好琴,蕉尾为名。
少女红着脸被按在琴桌前,手指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她看着底下人期待的眼神,请主人家把蕉尾换成承影。
剑是好剑,承影为名。
少女在红楼上舞剑,极绚丽灿烂的剑光,极漂亮鲜艳的红衣。
不知何处有琴声起,慷慨铮然,如裂帛,如玉碎。
只是偶遇,未曾琴剑相鸣,为何节拍与音律搭配得浑然天成?
大概是因为,她每一招每一式都是琴师所教。
琴剑未曾相鸣,但在他心里却已相鸣了千遍百遍。
剑光渐止,琴音也袅袅落下。
相玉儿抱着剑遥遥看向屋顶坐着的人。
他一身白衣,手指还搭在琴弦上,遥遥地,向她致一个笑意。
那舞剑舞得痛快的少女忽然丢下剑就跑了。
红楼主人还没来得及喊住她,就见那白衣琴师掠下屋顶,匆匆地追了过去。
于是众人心照不宣地认定,大约又是什么风月故事,一个逃,一个追。唉,今天的月牙,今天的灯,怎么它就那么亮呢。
呸,相玉儿,真没出息!
她一边检讨自己,一边脚下生风。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逃,却又逃得很是坚决。
她就这样坚决地逃了一会儿,发现后面好像没人来追了。
相玉儿心里涌上些不想承认的失落,低头叹了口气,脚步就慢了下来。
再一抬头,就撞上了柏翊的肩膀。
她条件反射又想跑路,清雅端正的白衣公子一把拽住她手腕碰瓷。
「你撞得我好疼,蝴蝶骨都震碎了。」
相玉儿匪夷所思地瞧着他,他面不改色地继续说完台词。
「你得赔。」
什么儿女情长,什么牵肠挂肚,什么郁郁寡欢。
被这无赖统统搅和得七零八落。
她气急,咬着牙,把荷包里的碎银子一股脑地都塞给他:「给给给,都给你,够了吧,赔完了吧,我可以走了吧?」
柏翊低头看她,形状好看的眼睛里盛满了月光,「不够,须得赔上姑娘的一生才行。」
她甩开他的手,不跑不逃,抱着手臂,冷冷地看着他。
「你究竟来干什么?」
少年温柔答:「我不来,你怎么刺杀驳君?」
她寒着脸,寒着声:「我不需要你陪。」
少年笑盈盈,白衣好似皎洁月光,「可我想常伴姑娘左右。」
她定定地分辨他神色,依然看不出破绽,依然像在倾诉衷肠,仍然好看地,想让人沉沦。
相玉儿忽然像泄了气的河豚,满心满身,只觉得好累。
「柏翊,这样有意思吗?」她问。
他含笑答:「有意思极了。」
相玉儿盯着不远处水面散漫的粼光,瘦肩孤颈,很疲惫的模样:「你与我合该只有一碗面的缘分,是我笨,是我傻,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硬生生把这点子缘分搅和成了孽缘。水里的月亮再亮,也不是真的。这道理,我早就该懂。」
柏翊沉默地站在她身后。
月光清浅,悄悄爬上少年白衣。
许是晚风有些冻,她搓了搓脸颊,抽了抽鼻子,继续道:「我从前喜欢逗邻居家的猫。没熟的时候,喂些好吃的,给些好玩儿的,它怯生生靠近一步,我就好开心。等熟了以后,小猫见了我就蹭我的裙子,我反而觉得无聊。你看,我之于你,大概就像小猫之于我,消遣而已,戏弄而已,既无真心,也无长情。我虽然笨,多少还剩一点骨气,已经远远地避开了你。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面前,为什么还要说这些让人误会的话呢?」
夜风吹动柏翊的衣袖,少年沉默地站着,像悬壁上孤零零的树,冷清到了极点。
相玉儿叹了口气,将荷包打开,取出小小一个白玉冠,递给他。
还清最后一点牵扯,大约就能再无瓜葛。
少年不肯接,亦不肯说话。
相玉儿把白玉冠放在他脚边,转身就走。
红衣单薄瘦削,像一枝料峭的梅,北风浓雪中瑟瑟。
她越走越远,也越走越急,像是害怕再犹豫一会儿,她就再没勇气离开。
那白衣少年始终立在原地,不曾追,却一直一直凝视着那道背影。
第三日,华灯满城,弦乐不绝,看热闹的人挤满了大街小巷。
吉时吉刻,重鼓为号。天子会携驳君登上城楼,受万民朝拜。
咚咚咚,重鼓响过三声。
街巷的绸店里,有个漂亮姑娘在试一身做好的衣裳。
掌柜的搓着手挺不好意思地站在一边。
这衣裳是他亲手裁的,按照姑娘半个月前的尺寸定制的。不知怎么,她这十几天了瘦了许多,连带着衣裳都显得空落落的,看着叫人怪心疼的。
姑娘倒没说什么,穿着新衣裳说挺好的就这样吧,结账道谢后,就走进了片片飞雪里。
连伞也没打一个。
掌柜的看着她背影愣了神,等她走远了才想起来忘了件事儿没说。
她那衣裳啊,上次陪她一起来的俊俏郎君已然付过钱了。
他让伙计追去还钱,可那孤单身影早就消失在都城的热闹人海中了。
咚咚,重鼓响过两声。
街边的面摊生意特别好,热腾腾的白气儿融化了飞雪,让那天上雪也来煲人间汤。
摊上坐了个姑娘,老板不小心把她那份面条上给了别人,她也不急不恼,兀自盯着人流发呆。
老板抽空看她两眼,心里犯嘀咕。
大概是什么娇贵的千金,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生多艰。这么大的雪连伞都不打,由着上好的衣裳被落雪沾湿,使肩绣上的皎月彩云都变成了黑月乌云。
他端着面捧到那千金面前,「您慢用嘞。」
千金拿起筷子挑一根面条尝尝,又拿起勺子喝口汤。
酱太咸,汤太甜,辣椒不够红,姜片不够冲。
一碗面,她从人多吃到人少。
老板得了空,擦干净手来和她搭话:「这面可还合贵人口味?」
她垂着眼如实告知。
老板想了一想,也诚恳道:「贵人您偏爱淡又偏爱辣,恐怕家中厨子不好当差啊。」
千金沉默了许久,嗯一声,然后笑了:「是啊,他真是不容易。」
咚,重鼓响过一声。
从宫门到城门的路两旁站满了兵士,兵士手中长矛交叉,将喜悦的民众挡在了身后,为御驾留出宽敞整洁的大道来。
拥挤推搡的人群中,兵士注意到了一个白衣姑娘。
姑娘瘦弱单薄仿佛水中浮萍,被周围人一会儿推到左,一会儿推到右,摇摇晃晃站也站不稳。
兵士生了恻隐之心,抬起手,扯着嗓子冲那边喊:「你们消停点儿!御驾马上出来了,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
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更高声浪的喧嚣之中,因为朱红的宫门沉而缓地打开了,八匹良驹拉动的御驾从黑暗中渐渐显出轮廓来。
在金色的御驾后面,一辆玄色车驾也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是天子和驳君来了。
不知是谁起的头,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响起,由于太不统一,几乎不能分辨民众们都在喊些什么。人们大声说着祝词,无非是祈愿天子和驳君万岁安康。他们不自觉地向前搡去,好像这样就能离万岁更近些似的。
飘着雪的冬日,兵士热得额头冒汗。他握紧手中长矛,勉力维持着秩序。当两辆车驾靠近时,他也忍不住扭过头朝那边看去。
那是睿智的天子啊。
那是慈悲的驳君啊。
谁不想早些一睹他们真容呢?
兵士是个忠于职守的兵士,因此他只是分散了片刻的注意力。
他回过神来时,又把长矛往前推了推,目光扫过面前狂热的人群,大声吼着要他们往后退。
人群稍稍有些不一样了,那个浮萍般的白衣姑娘不见了踪影。
总不会是跌倒了吧?这人山人海的,一跌倒可就难起来了。
兵士心里涌起了一丝丝担忧。
但他转眼就把这担忧抛到了脑后,因为空中出现了一道极亮极快的白光。
这白光如有实质,带着冰天雪地的寒,从干枯的树梢掠起,惊起了一片寒鸟。
寒鸟刚扑棱了翅膀,这道白光已然出现在了玄色车驾的上空。
如灌千钧之势,其势锐不可当。
喧闹的长街有一瞬间的寂静,人人都仰着头看这天降的异象。
兵士这才看清楚,原来那不是一道白光,那是一个握着弯刀的白衣姑娘。
是那个浮萍般脆弱的姑娘。
只是一眨眼,她握着刀劈开了车驾的顶篷。
兵士和他的同伴们这才反应过来,握紧了长矛冲上前去想将这刺客擒住。
他们刚迈开一步,车驾内碧色光芒大盛,几乎要穿过华贵的车驾,刺破人们的眼帘。
千千万万的民众像是畏光似的,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
玄色车驾内,相玉儿也闭上了眼。
她方才手握弯刀雷霆一击,几乎是必杀之技。
可是她没有击中驳君。
因为马车里空无一人,只有一颗夜明珠散发着幽光。
是被她当掉的春山如笑。
她一眼就认出了它,而弯刀也在这瞬间避无可避地击中了这上古神器。
春山如笑顷刻间碎裂,绽放出极绚丽的碧色华彩,它裹挟的影像声色也在同一时刻走马灯似的倒流回了相玉儿的脑海。
幼时家贫,她曾和野狗抢饭吃,在街头巷尾和大孩子打得头破血流,把最后一个完整的馒头带回去给哥哥吃。
哥哥从前不是虚弱的哥哥,哥哥为了救她跳进了冬天的河流,再醒过来的时候,就成了一阵风能吹倒的哥哥了。
破衣烂衫的两个孩子,真真是顽强至极,眼睛总是亮着,叫老天爷也不敢轻视其中流淌的生命力。
有大儒贺老,相中了这个贫苦的大孩子,想教他诗书,教他策论。
贺老只收男不收女,哥哥求贺老收下小孩,小孩却推着哥哥往前走,擦擦脸上的脏泥,笑嘻嘻:「我要去做女侠啦,学了武功,将来罩着你!」
哥哥咬着牙没回头,等妹妹走远了,他在贺府朱门内,哭得一塌糊涂。
此后又十年,游水国的左徒大人惊才绝艳,清名天下知。
黑市里的刺客榜悄悄更新,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拔得头筹,据说她喜着红衣,性格极冷。
左徒大人自己开门建府,找回了妹妹,妹妹被前来做客的国君看中,一个关于权力斗争的故事就此铺开。
姑娘是刺客,从前杀的都是恶人,宣平侯要她杀邻国肱骨,她不太忍心。
于是姑娘逐一排查,看谁私德败坏、品行有亏。
月黑风高,她拎刀去杀人,高高屋檐上,坐着个貌美少年。
少年一身玄衣,眼见是个顶贵气的公子。
她以为是这家良臣的小儿子,脚下一滑,要从屋檐上摔下去。
少年拽住她手腕,被她一起拉了下去,摔在庭院正中,惊起一滩灯火。
他们俩低着头挨训,一黑一红,模样个顶个的好。
鬓发斑白的主人问他们半夜三更翻屋顶做什么。
她手指按了按刀鞘,想着要不直接砍上去算了。
少年却伸手过来,握住了她的手,十指相扣。
然后少年坦坦荡荡一笑:「我与邻家妹妹情投意合,无奈家人并不同意。我们预备私奔的,却在您家屋顶滑了一跤,真真让项大人见笑了。」
她心里惴惴,要知道这姓项的最是严肃教条,风月情事只怕会让他更生气。
项大人沉着脸,却放了他们一马。
甫一出门,少女就甩开了少年的手。
少年笑盈盈:「女侠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
从来没有人喊过她女侠,喊她女贼的倒是很多。
少女一愣,儿时遥远的诺言撞上她心扉,她垂着头丧着气,心想怎么就混到了如今这步田地。
少年又问:「你可知道项大人为何愿意放过我们?」
少女冷面冷语:「这姓项的元妻死后不满三月他就另娶新妇,可见是个薄情寡义、贪图颜色之人,大约是看你我颜色甚好,心慈手软了罢。」
少年摇头,似笑非笑,「非也非也,项大人的新妇才是他真正的元妻呢。新妇李氏是他邻居家青梅竹马的恋人,原本该凤冠霞帔入项家的门。但刁蛮霸道的赵氏也看上了项大人,赵氏以父兄官权相逼,以李家性命相挟,硬生生赶跑李氏,成了项大人的元妻。项大人隐忍多年,为官清正,致力于清除欺男霸女的豪庭之流,当真可算是直臣清流了。」
红衣少女握了握手中弯刀,睁圆了眼睛,像在庆幸这把刀没有砍向项大人的脖子。
然后她问:「你是谁?」
少年笑着眨眨眼,乌黑纤长的睫毛晕开一片月光,「我啊,我是柏翊。」
她又问:「你来干什么?」
少年温柔地瞧着她,答:「我来报恩啊。」
此后柏翊一直跟着她,黑衣黑马,像地府的无常。
偏这个黑无常有一双桃花眼,总是温柔带笑,屡屡让这没见过世面的小刺客红了脸。
他带着小刺客吃吃喝喝,拨浪鼓摇摇马,糖画泥人纸风筝,把她灰暗的童年补得五光十色。
温柔乡让弯刀生锈,让轻功变慢,让小刺客渐渐化去了一身的冰霜。
小刺客做任务懈怠了,宣平侯自然十分清楚。
他轻言细语地恐吓小刺客,说除了蛊虫之外,他还给左徒大人服了药,一日不饮解药,她哥哥一日不得安眠。
小刺客丢开弯刀,泪汪汪地上去扑打尊贵的侯爷。
侯爷随便她做困兽之斗,提醒她:「我若是你,就会立刻去杀邻国的国君,让你哥哥少受些苦。」
小刺客磨刀霍霍,不再想所谓公义道德,她只想她哥哥活着,夜夜好眠地活着。
然后就是那场说书先生口中的刺杀失败。
其实他说的不全对,并没有什么驳之神力震慑,只是柏翊陪她演了出戏罢了。
她去刺杀妗水国国君,红衣萧飒,弯刀如冷月,眼看着就要割断国君的喉咙,却被柏翊的剑尖挡了回去。
柏翊站在国君身边,说出事先准备的台词:「姑娘,驳君有命,命我阻止你再造杀业。」
你看,他这样会演,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台词,他也说得好像真有此事。
这浑然天成的演技瞒过了宣平侯,他在宫殿里跳脚,大骂驳君忘恩负义,被一个骗子耍得团团转。
小刺客听得稀里糊涂,而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宣平侯指着她说:「你去,把驳君给我杀了!」
小刺客觉得他发了疯。
她回到了哥哥的宫院,院子里有人在喝茶。
一身玄衣,笑容好似月光。
是柏翊。
柏翊正和左徒大人品茗下棋,见她来了,起身告辞。
「那么,就拜托你了。」她的哥哥这样说。
玄衣少年亦向他欠身致礼:「不必客气。」
她愣愣地看着少年掠过树梢、掠过宫殿、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星夜,才想起来问哥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哥哥一脸的不可说,只是笑答:「他人甚好,你若喜欢,我很放心。」
小刺客之后时常想起哥哥的这句话。
天下人都说,游水国的左徒大人惊才绝艳,那么他说的话,他看的人,必定不会有错。
玄衣少年依旧陪在她身边,陪她练武,陪她看山看水。
她有时望着玄衣少年,一忽儿迫不及待地想把这句话告诉他,一忽儿又低下了头把话咽了回去。
小刺客身在江湖,很有几分豪爽,但内心仍是个小姑娘。
小姑娘想,情情爱爱的,怎么能由女孩子先开口呢。
少年不说,她也不说。
可是,当她杀去国都,被心爱的少年一剑刺穿心口的时候,她才悲伤懊悔,她还有句话没来得及说呢,怎么就再也没机会说了呢。
碧色光芒渐渐消退,相玉儿抬起头,泪流满面。
她的从前平平无奇,最大的惆怅无非是喜欢上了一个求而不得的少年。
和她的现在何其像,就连喜欢的少年也没变过。
这样的英俊温柔,这样的,断人心肠。
马车外有弓箭上弦的声响,相玉儿从车厢中一跃而起。
万箭齐发,破空之声铮然。
一身白衣的少女握着弯刀,刀光冷冽,衣袖划出锋利的弧度,将箭矢斩落在半空。
少女脸上还带着泪痕,眼神却冰冷,她挥刀泼溅出鲜血,对着恐慌惊惧的人群大笑:「柏翊,你出来啊,你当初能欺我骗我甚至杀了我,为何如今只敢拿春山如笑来应付我?你不是要守卫天下和平,不是要给万民安泰么?我当着你的面杀光你子民,你又待奈我何?」
无人应答。
她握着刀杀势不减,成百上千的卫士,没有人能拦住她。
血花四溅,染上了少女的白衣。
最初只是红梅两三点,而后越聚越多,分不清是少女的血还是别人的血,一身清冷白衣彻底成了灿烂红衣。
少女衣袖在风中振振作响,有如地府旗帜,更像恶*索命。
那张顶顶漂亮的脸上血痕交错,一双眼睛冷酷冰凉。
「好一个缩头乌龟,好一个……驳君!」
城墙上,沉重的箭弩被卫士扛了上来,塞进火药,安上连珠,箭镞对准了浴血的少女。
相玉儿踩着刀戟跃起,红影掠上城墙,杀神一般,挥刀就要砍向十发箭弩。
卫士极惊惧,箭弩若破,火药炸开,只怕所有人都尸骨无存。
画面仿佛静止。
雪花凝在半空,云气渐渐生起,一团柔柔云雾中,有一人一马破空而来。
人着白衣,宛若谪仙。
马有一角,生虎牙爪。
黑马长啸,声如鼓音,所有人手中的兵器齐齐落了地。
白衣少年在空中行走,踏着云气,如履平地。
白衣飘飘,宛若谪仙。
他看见他心爱的姑娘,一身滴血的红衣,煞白着一张脸与他对望。
他轻轻叹息。
万人噤声,连天子御驾也寂静无声。
柏翊开口,声音沙哑:「从前有个姑娘问我,她之于我,是否如同邻家小猫,只是消遣,只是戏弄。我想了许久才想明白,她之于我,是珍宝,是明月,是唯恐弄丢又害怕枯萎的娇嫩花儿,让我小心翼翼,不知道该如何呵护。」
相玉儿远远地站着,安静地听,看不清神情。
良久,她说:「你总是能把假话说得那么真。」
柏翊沉默了一会儿,自嘲地笑了,「是啊,我总是骗你逗你,什么都瞒着你。你憎我怨我,乃至再不信我,也是我自作自受。」
相玉儿没再说话,像是默认。
柏翊还待说什么,却看见那红衣姑娘好像站立不稳,如同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般,从高高的城墙上坠了下来。
白色衣角翻飞,柏翊慌忙伸手抱住她,她肩背处的血将他指缝浸透。
素来镇定从容的少年慌了神,伸手去覆她伤口,纯白的光圈一层层弥漫,他怀里的姑娘始终紧紧闭着眼睛,嘴唇苍白。
好久,姑娘才翕动眼睫,睁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柏翊将她温柔地看着,看见那双眼睛眨啊眨,眼圈一点点发红。
他心爱的姑娘正望着天空,攥紧了衣袖,无声地哭泣。
柏翊忽然觉得自己是个混账。
他将姑娘打横抱起,旁若无人地,从御道往前走去。
「陛下。」他对着金色御驾唤一声。
御驾里有人在深深地叹气,随即传来天子苍凉的声音,「你去吧。」
他不道谢,仿佛理所当然似的,抱着他脆弱如浮萍的姑娘,扬长而去。
一千个一万个臣民沉默地目送那白衣少年离去。
原来那就是驳君。
原来那才是驳君。
人们都想象悲悯众生的驳君大约会像庙里的神佛。
慈眉善目,白发苍苍,无悲无喜,无波无澜。
可他们又忽然觉得,护佑天下的驳君就该长这个样子。
一个如清风明月的少年郎,爱世间万物,也偏爱世间一人。
驳礼起了变故,这变故尚未传到都城以外的地方去。
而游水王宫的僻静宫院里,左徒大人的门悄悄地打开,又悄悄地关上。
这处宫院很清静,没有雕梁画栋,只有翠竹几株。
相无渡正在摆一局棋,灯影斑驳。
听见门开合的声音,他似乎并不意外,头也没抬,轻声说:「来了啊。」
相玉儿已经换了一身干净衣裳,雪白的衣裙,长发无饰,仿佛要吊唁。
相无渡伸手摸摸她发顶,瞧着她发红的眼圈,说:「我就知道你今天要掉眼泪,也知道你今天肯定要伤他的心。」
柏翊远远地站在门口,脸庞沉在阴影里,让人看不清神色。
相玉儿嘴唇苍白,眼睛却明亮,执拗地盯住哥哥,要他给一个说法。
瘦弱的左徒大人裹紧了大氅,将房门推开,北风争先恐后地灌了进来。
仿佛只有在这样冰凉又清醒的寒意里,他才能将回忆慢慢说给她听。
他年纪轻轻就官拜左徒,也是机缘巧合。
那时宣平侯刚从兄弟厮杀中浴血登上王位,急需提拔自己的亲信。
他无门无派,孤身一人,又很能想些良策,是个直臣的料子。
宣平侯要立威,要敲打老臣,就给了初出茅庐的少年一个机会。
而年轻的左徒大人幸不辱命,施*有方,驭下有术,为人不卑不亢,很快成了侯爷的左膀右臂。
在某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小侯爷来他家喝酒。
小侯爷醉眼惺忪,搂着他肩膀笑嘻嘻,说他年少时救下了一个人,这个人和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驳重信重义,必定知恩图报。有了这份恩情,他就能得到驳的支持,游水国就能享万世太平。
可小侯爷再喝一杯酒,似乎又很生气,勾住他脖颈,温热的酒气扑在耳朵上,让人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小侯爷说,无渡啊无渡,我拿你当亲兄弟,你可不许背叛我,你不能坑我害我,不能像我堂哥那样背信弃义。
众所周知,宣平侯只有一个堂哥,那就是当今天子。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天八卦撞晕了头,一边拉开和小侯爷的距离,一边还在思考这两件事情有什么联系。刚想抬起头再多问两句,而那厢,据说生性多疑的小侯爷已经瘫倒在他家石桌上呼呼大睡了。
再后来,他接妹妹回家。
从小就冲在前头保护他的妹妹长大了,果然成了女侠,一身灿烂的红衣,也一身的伤疤。
某天她练剑被做客的宣平侯瞧见了,城府极深的小侯爷看了她半晌,没有让人惊动她,转身,就想了一个釜底抽薪吞并邻国的计谋。
他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表面却要装得风平浪静,淡淡推拒道:「家妹草莽出身,愚笨不堪,恐怕难当大任。」
小侯爷坐在高高的王座里,抬手笑道:「爱卿不必谦虚,本侯听说你妹妹在那刺客榜上排第一,实在是最佳人选。」
小侯爷拍了拍手,宫娥端进来两粒药丸。
他笑着说:「我知道你爱妹心切,不会轻易答应。但是在接风宴里她已服下了蛊虫,本侯若是不开心,她或许就会死在你面前。左徒大人,你这样聪明,自然知道孰轻孰重。」
一个只待他走入的陷阱。
设下陷阱的人笃定了他不会轻视妹妹的性命。
年轻的左徒大人沉默了许久,才听见自己的声音说:「臣自然是听侯爷的。只是,家妹刚烈,只怕宁愿自尽也不愿受人胁迫。还请侯爷瞒住她,让她以为蛊虫在臣的身上。」
漂亮的小侯爷饶有兴致地盯着他,「哦?那么你妹妹是把你看得比她自己还重了?」
他木然点头:「是啊,她就是这样,永远把在意的人放在自己前面。」
小侯爷召来了妹妹,妹妹失控地将弯刀摁在侯爷脖颈。
侯爷张口说了些什么,然后她朝他看来。
他轻轻地点了一点头,于是那刀锋就颤了颤,无力地落在地上。
那一身红衣的女侠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
冰凉华丽的殿堂里,她涕泪交加,像个孩子。
一样的勇敢无畏,一样的,有着软肋。
然后她站起来,仰着头为他擦干净眼泪,然后打开门,向着宫外走去。
他一直凝视着她的背影,仿佛穿过了十几年的岁月,他仍然是那个站在门后,看着妹妹一步步走向另一种命运的,小小少年。
刺眼的阳光照进了宫殿,左徒大人闭了闭眼睛。
人人都说,左徒大人的妹妹愚笨、草莽,是他最大的污点。
无人知晓,其实她勇敢、决断,是他最大的依靠。
再后来,他逐渐窥探到了侯爷的秘密。
关于驳,也关于那个获救的小女孩。
某日,他见到柏翊出现,少年脚底还有尚未消散的云气,一身玄衣,一匹黑马。
柏翊生来一双凉薄的眼睛,偏偏对他不通人事的妹妹笑成弯月。
他心里生出几分猜测,于是请玄衣少年喝酒,谈《山海经》的传说,谈周天子的功德。
玄衣少年见他旁敲侧击,直截了当地问他要做什么。
他说,他要借驳之神力破一个死局。
驳之神力可起死回生,母体已死,蛊虫必亡,他想用这个方法救回妹妹的性命,也想还她早该拥有的自由。
柏翊沉默许久。
他大约能猜到少年在担心什么,愧疚道:「这一招虽能解开死局,却会让你遭受误解。」
玄衣少年抬起了头,却说:「我并不害怕误解。我只是在想,原来她一直背负着这样沉重的事情,她该有多辛苦难熬。」
他愣住。
就听见少年望着月亮轻轻叹息:「我只是……有些心疼她。」
故事讲完了,相玉儿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过了许久,她才站起身,往门外走去。
路过柏翊,路过相无渡,路过门口蹲着的小贼。
冬风不识趣,吹动少女衣袖,吹动少女发梢,妄图挽留,妄图致歉。
世事纷纷扰扰,误会纠葛太多,谁伤了谁的心,谁又为了谁好。
算不明白的,都是糊涂账。
斜里伸出一只手,小贼颤颤巍巍地拉住姑娘裙摆,小心翼翼道:「你若是还生气,不如骂我出气。我哥哥喜欢你喜欢得紧,你别让他再难受了。」
相玉儿瞧着这唇红齿白的小贼,发笑:「我气他们把我当傻子瞒得密不透风,但你又没做错什么,我为什么要骂你?」
小贼被她问住,想了好久,才答:「若不是我小时候溺水被你救起,他就不会找你报恩,也不会喜欢上你,更不会杀你以解蛊*,让你记恨上他。」
世间因果千百种,良缘一线相牵。
那年寒风瑟瑟,破衣烂衫的小孩勇敢地跳进水里,去救一个比她更小的小孩。
缘分兜兜转转,小孩长成娉婷少女,小小孩的哥哥坐在屋顶等她,等着做一次她的情郎。
相玉儿不说话了,苍白的脸上有了淡淡的血色。
小贼于是又说:「宣平侯以为他救了我,把天子视作偷窃秘密的罪人。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哥哥护佑的是天下安宁,根本不在意做的是谁的座上宾。我们家的人都这样,爱天下万物时,万物都不入心;独爱天下一人时,才觉出天下的可爱之处。」
相玉儿也蹲下来,看着她,问:「那么你也一样吗?」
小贼害羞地红了脸,答:「宣平侯自以为他救了我,可他并不知道,那只是因为我想在他身边长大的缘故。也正是因为我,哥哥才愿意对他手下留情呢。」
相玉儿伸手揉了揉小贼圆鼓鼓的脸颊,站起身来要走,走到一半,停下来冲众人挥了挥手:「我走了啊,有空来吃面。」
话都说不清楚,也不知道是对谁说的。
小贼说她不爱面食,左徒大人表示懒得出宫。
只有那黑暗中的白衣少年郎兀自笑弯了眼睛,悄声应一句好。
清水镇老板娘的面摊重新开了起来。
不同的是,这次忙前忙后的是一个白衣少年。
少年手指修长又洁白,面团揉得很劲道,菜码切得也整齐。
唯独味道有点问题,偏淡又偏辣,没有从前老板娘调的味好吃。
面摊生意跟以前差不多红火,不过老少爷们儿少了些,大姑娘小嫂子多了许多。
呸,都是些看脸的人!
吃面吃得最慢的老主顾愤愤不平地咬着卤蛋,又在白衣少年过来收拾桌子的时候问一句:「老板娘什么时候才出山啊?」
白衣少年擦着桌子,闻言笑一笑:「等我把她娶进家门,也许她就会出山。」
老主顾「嘿」了一声:「我说小伙子,你答问题就答问题,怎么还秀恩爱呢?」
白衣少年故作羞涩地低下了头,捧着一摞碗去汲水洗涤。
刚放下碗,就听见老主顾喜滋滋的声音:「老板娘,好久不见哪,我刚还和你家伙计说起你呢!」
她出来了?
柏翊直起腰来。
相玉儿笑盈盈地和老主顾打招呼,又问他:「我家伙计的手艺怎么样啊?」
老主顾四处看看,估摸着柏翊正洗碗听不到,小声道:「要我说啊,比起你还差远了。」
相玉儿就笑。
老主顾又唠了会儿嗑,才意犹未尽地去上工了。
相玉儿转身,撞到了少年的衣襟。
「干嘛呀你,吓我一跳。」她抱怨,往后退一步。
朝阳升得很高了,街上只剩下三三两两的人。
没人注意到,城镇一角的面摊里,白衣少年靠近了老板娘,在她耳边问:「我是你家伙计?」
老板娘不答。
少年于是更低了头,气息枕在她肩膀,笑意藏也藏不住:「那你什么时候付我佣金?」
老板娘转身要走。
少年眼疾手快地拽住她手腕,将她整个儿从后面抱住。
多霸道的姿态,他却在小声撒娇:「你给个期限嘛。」
老板娘的脸颊整个儿红透了,跳着脚要他松手。
这两人容貌过于出色,路过的人八卦兮兮地抬起头观察,生怕错过什么好戏。
少年笑着说一句:「家事而已,别看了,散了吧。」
顺手揽住她肩膀往小院里带,砰的一声关上门,将看客视线隔绝在外。
小院里红彤彤的,窗台上贴了喜字。
窗台下几盆鲜花,初初吐露新芽。
一只公鸡蹦到石桌上,和那张绣到半途的鸳鸯大眼瞪小眼。
有喜鹊叽叽喳喳栖息在树梢,侧耳听透出屋子的人语笑声。
从秋到冬,从冬到春,故事从清水镇开始,又在清水镇继续。
一年又一年,说书人的话本换了新词。
说那宣平侯始终未有妻室,左徒大人也一直住在王宫。宣平侯再也不提吞并邻国的梦想,他的野心变得很小啦,小到刚好放得进左徒大人的一座宫院而已。
游水国的黑衣小贼长大了,学聪明了,也看清楚了,她心里喜欢一个人,但这喜欢从来就只是徒劳。于是国都之中,天子脚下,多了座神仙庙,里面住着黑衣少女,喜临水自照。
再就是盛大驳礼上的无名刺客,明明是来搞刺杀的,不知怎么反而拐走了刺杀对象,可见是个二流刺客。二流刺客金盆洗了手,隐居在小镇摆面摊,有个白衣伙计,甚是可心。
看官啊看官,人间风月千万种,有的云山雾绕,有的乌云蔽月,最喜是冰释前嫌、花好月圆,也是可遇不可求。唯有亲身历一遭,方知纸上半卷,尚浅尚浅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