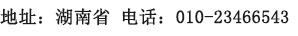喜鹊颂
在神木平阔的北方村野,喜鹊远远大过麻雀的数量。它们把优美而椭圆的巢窝做在高高的杨树上,而四季安然,其建筑似乎比人类更技高一筹而符合自然的规律,只要不把杨树伐倒,这些巢窝就几十、几百年地存在,它的寿命应该比树木本身更为长久。人类的建筑最伟大最古老最与自然亲近的还是*土地上的窑洞,凿石而筑、挖土而居,不用一砖一瓦,冬暖夏凉的舒适不借助现代化的一叶鳞羽,它才是自然主义的杰作,它才有资格和鸟巢一比高低,而其它建筑,辉煌的罗马金字塔,威严的美国白宫,形同水泥森林的上海摩天楼群,把钢筋水泥悍然灌进深深的土地里,似乎都不堪时间风沙的侵蚀,一点也不符合“安居乐业”的本意,不符合人性所能接纳的设计。而喜鹊窝,它的根基就是杨树撑开的枝杈,一般是三根树杈中间开始搭建,它们似乎远比人类更早地懂得“三足鼎力”“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这些自然的常识,在狂风横扫的春天,巢窝也不会被吹落下来,甚至连做巢的材料——任何一根杨树枝也会纹丝不动。大雨滂沱也无损于巢窝的坚固,会有枝叶为它做庇护,雨点顺着树干和叶子滑落到地面上,而无法在巢窝上驻留。它们的头顶便是天空,一只公鹊和一只母鹊卧在夜晚的巢窝里,如同一对情侣相拥在旷野里数明亮的星星。喜鹊才是“以天地为屋”的忠实践行者。
因为无法一睹高高在上的鸟巢,它神秘的像一件大自然的完美杰作。这样的机会还是来了,在一条煤车往来的道路旁,我和惟岗看到一棵四、五米高的榆树上,坐着一个硕大的喜鹊巢,这让我们做梦都想看看鸟巢的意愿终于付诸实践。这是一个废弃了的巢窝,和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是多么的不同,网上的喜鹊窝是深而敞口的,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内室宽大和毛草凌乱,从外面看粗黑的巢窝很大,两手环抱也不能够着,其实里面却是小而舒适的,内室如一只粗瓷大碗状,那些树枝看是随意搭建,实际上每一根都交叉在另一根树枝上,这样一层层呈弧形围拢起来,堆积的很厚实,虽然没有什么来粘连,你却用力也抽取不出任何一根树枝来,喜鹊做窝伟大的构思源自哪里,我们仅仅靠“本能”来解释动物的行为很有些牵强附会。最让我们惊奇的发现是,鹊窝并非是敞口朝天,而是完全编织回来的,像盖子一样,只在巢顶的侧旁,开一个仅供出入的窝口,像极了农人编织的一个小口柳囤子,里面光洁而温暖,垫着野草茸茸的叶茎。很好地避免了来自天空鹰类的侵袭和雨雪的浸渍。它为什么要把自己苦苦建筑的家抛弃呢,直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巢窝早于道路的历史,在道理未开通前,喜鹊已经把家安在这个阳光热烈的平坦处,过着风轻云淡、怡然自得的快乐生活,它们三五成群,也单独落在地面上,农人的玉米杆堆和拴牛的向阳处,喳喳寻食,有时跳到牛背上,如同在草径上行走。农人热爱黑白分明的喜鹊,从不驱赶它们,它们是乡村水草平安和生活吉祥的象征。道路的入侵迫使喜鹊离开这里,我们看到这条路上,几乎是煤车专运线,一辆车和另一辆车穿行速度间隔都不超过一分钟,日夜不停息地轰然而过,洒下的煤尘厚厚地罩在土地上,空气给人一种灰暗的窒息感,喜鹊只能弃窝而去,这种强者糟践、欺凌弱者的景象,实在不是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所该有的面貌和行为。
喜鹊的社会不是法制的社会,并没有贫富悬殊,没有阶级仇恨,没有战争侵略,不用阴奉阳违、言不由衷,不论雄雌老幼,不管身居高枝还是在大地上跳跃,喜鹊的鸣声只有一个永不变异的“喳喳喳”的调子,音韵响亮而底气十足,一副善调高奏的姿态,所以古人曾称喜鹊为“圣贤鸟”,就是取其声调恒定不变之意,如果用现代诗来描述它,就是“一生只唱同一首歌,这歌里充满了欢乐”。它们不持有什么身份证可以随意在乡村的大树上落户,有时同一棵杨树上,赫然座着两、三个鹊巢,它们不领取什么结婚证的“一夫一妻制”却能够把爱情进行到底,每年三至五月间,是喜鹊孕育后代的 时间,早在冬天,它们已经为孵化雏鸟做准备了,主要精力用于巢窝的营建,一个巢窝的建筑,至少也得用去上万根约一至两尺长状若大拇指粗细的枯树枝,而且全靠嘴来完成,又和人类社会中“靠嘴吃饭”多么不同,“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定给你打开另一扇门”这句话多么适合在这里感慨。喜鹊没法借助什么工具把树枝据下来,只能飞到地面上叼风吹败落的或农人折下来当干柴用的树枝,上万根树枝,一只公鹊带着一只母鹊,从树上到地上,又从地上到树上,来来往往得五千多个回合,而且有些树枝是远一点的地方叼过来的,中途体力不支时要停下来歇一歇再继续飞,有些周而复始的意思,这不是鸟类中杰出的艺术家是什么,这不是一种爱的支撑又是什么,一个鹊巢通常要用一百多天才能完成。我们常常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思想,其它动植物都是一种无意识的物性和本能来“引导”着它们的作为和形态,那么,喜鹊做巢,这样的解释并不能够让人信服,无疑,巢窝是在喜鹊做窝前就存在于它的意识中,这样说,诸如喜鹊等鸟类也是有思想的,它们要把巢窝做得稳固、美观、耐用、经得风霜雨雪,躲得雕鹰的血腥入侵,适于 的居住,这些等等人类思考了再思考的问题,其实喜鹊叨起 根树枝搭窝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完全是“先知而后行。”
喜鹊孵化时,由公鹊照顾母鹊的饮食,一般产蛋时间是在5至8天,每天产一个淡蓝色带些灰黑小斑点的椭圆形鹊蛋,一位和我同样热爱自然的朋友告诉我,喜鹊孵蛋和母鸡抱窝基本一致,母鸡孵化是用21天,喜鹊是22天,她和科学家的说法有些出入,科学家认为喜鹊孵化用时18天,我没有细致的观察结果,所以不能够确定她们之间谁更准确。她还告诉我,小时候呆在乡村,有一年喜鹊趴窝,她爸爸趁喜鹊去外面寻食时,偷偷爬到屋前的树上去,把喜鹊蛋拿掉,放几个鸡蛋进去,当孵化出来便爬树上把鸡仔拿走,它们就死命盯着鸡仔要把它们的“孩子”叼走,而且只要再放蛋进去,它们照样安静地孵化,而且是夜以继日地不睡, 喜鹊被人为的折腾,经受了长时间的孵化而被累死了。当它们知道不是自己的蛋时,还要去孵化,这算不算高尚?所有的喜鹊都是这样的行为,无疑,它们不需要谁来指手划脚、发号条令规范自己的行为,那靠什么建立起这种井然有序的“喜鹊秩序”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基于爱,喜鹊把造物主赋予人类也赋予鸟类的这种爱无损分毫地延续下来,而且它们保持着高度的自治自救自律自爱的生活方式,却是有着几千年辉煌文明的人类始终遥不可及的一种理想状态。
喜鹊的样子很优雅,这种优雅体现在它们从容不迫的神情里,它们很在乎自己的仪表,总是干干净净,大大方方,翎羽顺直而光滑,是鸟类中的君子,如惟岗描述的“像英国的绅士”。两只翅膀的顶稍和胸脯底下呈亮白色,其它皆黑色,这仅是远观的印象,一次我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几只喜鹊,它们似乎不在乎畏畏缩缩的我,依然我行我素,迈着阔步,四平八稳地在地上寻找草籽谷粒,我继续靠近,想清晰地观察造物主是如何赋予喜鹊如此美轮美奂的形体,造物主这老头,一定是位无上荣光的艺术家,他的所有行为都充满了美的特质,让万物之于世界,并不仅仅局限在功用的范畴。当我距离喜鹊四、五米远时,它们修长的尾巴一翘一翘,开始跳着向后退,似乎明白人类并没有残害喜鹊的任何历史记录,但它们还是对人这个反复无常的物种保持了足够的防备和警惕。它们蹦蹦跳跳,喳喳喳地有些热烈地交谈着我无法听懂的语言,我猜想它们是为阳光与爱情而歌,为找到一块谷粒丰盛的土地而歌,为小雏雀能够扇动翅羽而歌,为生命的日日新而歌,绝不是为股票和汽车而歌,为现代化的标志——高大的烟囱而歌。有谁见喜鹊追逐着汽车的尾气而快乐飞翔呢。多么繁华的都市,多么富豪的居室,都不会找到任何一只喜鹊的影子,喜鹊没有人类贪婪的嗜好,它们对人类的创造漠不关心,甚至一点兴趣都不会有,它们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不该去哪里。它们居住着和祖先一样的巢窝,吃着和祖先一样的草籽,活动在和祖先一样的场所,唱着和祖先一样的歌,它们的声调单纯而清亮,每“喳”一声,尾巴跟着上翘一下,显得非常气宇昂扬,其情形就像我和惟岗平日里醉心于大谈宇宙与人生,神采飞扬而目空一切。在阳光下,喜鹊漆黑的羽毛泛着幽蓝的色泽,从树上飞落到地面,又从地面飞回树上,似乎一种坚定的信念和生活的规则指引着它们,这样周而复始而又朝气蓬勃。
喜鹊总喜欢与农人为邻,农人种植的五谷杂粮,同时也是它们喜好的美食,谷堆旁,场院上,大树下,牛圈里,农人撒落的黑豆、玉米、荞麦,牛粪里没有消化的草籽谷粒,就是它们的食物,这些简朴而自然的地方,就是它们获得快乐、自由的天地,这里有足够多的食物让它们吃住无忧,有足够多的草地和树林供它们唱歌纵舞。但它们并不像猫狗鸡一样,依附人类而生存,世界上没有家养的喜鹊,它们还是未经人类驯化的野性十足的鸟类。农人和喜鹊互生互存的关系,是人与鸟类和谐共处的一个绝好样本。至今我仍然相信,喜鹊不会和胡燕一样落在屋檐下,只见过它们落在脑畔上,院子里的大树上。我老家人就叫喜鹊为“野鹊子”,它们对人类一直若即若离。同样是那位热爱自然的朋友告诉我,儿时捕了喜鹊来笼子里圈养,但它绝不会啄一粒米,喝一口水,哪怕把食物送到嘴跟前,强按着它的头部,喜鹊是不会屈尊于你的掌中,成为衍生物。它在笼中上下冲突,羽毛凌乱、脱落,使尽浑身之力来挣脱这“生命之桎梏”,哪怕这挣扎,终是一种徒劳。没几天喜鹊就死去了,大喜鹊盘旋周围,声声啼血,累到气绝身亡。“不自由毋宁死”,其情形一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侠人志士。无论大喜鹊,小喜鹊,甚而推论,从喜鹊的始祖至它们无穷尽的子子孙孙,一律视天性为命。所以抓捕一只喜鹊,等于毁灭一个喜鹊家族。喜鹊,以及麻雀,天生就是野生的,任何方式的驯养都会以失败告终。它们延承着从前喜鹊的生命形态,更是以后全部喜鹊的生命形态。它们卓然,独立,自由,开一切生命形态的引领和先启之河。它们永远是热爱并保守天性自由的一群鸟。喜鹊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很令人羡慕,从不见它们像老鼠一样聚敛食物,没有固定的进食时间,也没有工作,一边玩一边啄食就是它们生命的常态,顶多返回巢窝时衔一截垒巢窝的枯枝或喂养尚不会走动的小雀的食物。大风大雨时,它们就会安静地呆在窝里,静待天晴。它们似乎只关心风霜雨雪的自然壮歌,只关心春夏秋冬的荣枯更替,与自然违背的事物,道路、城市、现代化,便也是它们极力厌恶和远离的,它们带着毛绒绒的雏鸟,在风清月明的乡村和树林间跳跃、飞翔。喜鹊从不舍近求远,它们的简单生活本质上与人类的幸福如出一辙。当我们站在大地上,仰头注目树上的巢窝和喜鹊时,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卑微。在卑微的人类面前,喜鹊就是一种始终如一的高尚的鸟,它们比人类更自由、更幸福。
北城北城,本名王静,年生于陕西省神木县沙峁镇铁炉峁村。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神木县作家协会主席。在《中国作家》《诗刊》《中华散文》等杂志发表作品。有散文集《北城散文选》《北城微语录》《爱默生说》,诗集《把星星画在白天的纸上》。北城的作品对宇宙生命及人类生存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认知,并进一步阐释了“自然宇宙法则就是人类的 法则”这一创作主题。文风恣肆,思想精深,充满了一种生气勃勃而激荡自由的“北城风格”。关于我们……打造 的地方文化圈
我们一起携手挖掘府谷文学
原创
府谷文学
平台编辑
王磊白耀文闫敏
投稿邮箱
qq.